醫圣張仲景秘傳的經方,究竟能不能加減?如果能,該如何加減?
發布人:奧姆龍 時間:2020-07-02 閱讀:1854
“在中醫界,很多人將醫圣張仲景傳下來的方劑尊之為經方,對于經方的使用,很多人認為經方要原方劑量會更好,不適合加減。但也有很多人在經方的基礎上進行了加減,而且也屢試不爽。那么,經方究竟能不能加減?如果能,該如何加減呢?請看下文:”
《傷寒雜病論》經方廣受學者關注,在經方研究方面,形成了幾個備受爭議的問題,第一個便是經方能不能加減。
有的學者認為經方十分經典,一味不能增,一味不能減,不能輕易改動,必須用原方原量。有的學者認為經方可以靈活運用加減。
筆者從醫二十多年來,常常聽聞第一種觀點。二十多年前,在成都中醫藥大學讀大一之時,便偶聞師兄傳言有某某醫臨證只開經方,運用經方從不加減,嚴格遵從《傷寒雜病論》原方原有味數,并于言語之間,大有夸贊褒揚之意,稱之為中醫高手。筆者當時方值習醫之初,沒有臨證,所見鄙陋,聞此亦頗為神往。
然而,后來從實習到畢業之后行醫,二十多年來,現實之中,所遇中醫同道成千上萬,從未遇到過用《傷寒雜病論》經方不加減者。很多前輩,臨證水平很高,在使用經方時,也是靈活化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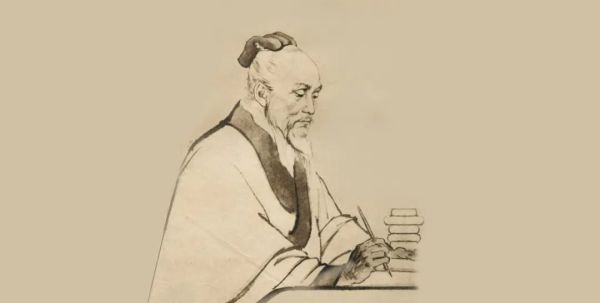
而筆者所遇到的或筆者朋友、學生所遇到的多年講授《傷寒論》的專任中醫教師,在臨證之時,也沒有偏執經方原方不加減的,不少《傷寒論》名師臨證開方,也并不僅限于用經方,甚至有的用后世方比用經方更多。
以上情況,相信大多數學者也有目睹耳聞。傳聞與大多數實際不符,讓許多中醫后輩學者困惑不解。筆者二十年前也是困惑者之一,困惑于為何研究《傷寒論》的老師大多數時候并不開經方,或者為何不是經方原方派。
近幾年來,“經方學派”大熱,不少學者持經方不得加減的觀點,甚至有的學者認為用經方不加減就是高手,認為開經方原方不加減就是“漂亮”,這樣的觀點影響越來越大。要知道,臨證處方,不是看方開得“漂亮”還是“不漂亮”,關鍵在于是否有效,若無效,經方又有何意義?
《傷寒雜病論》之后一千多年來,名賢輩出,后世方書汗牛充棟,不少經典方劑亦由此而出,在臨床亦有大功用。真正為病家考慮的醫者不該有門戶偏見,就算是民間偏方,某些情況下,有大功用之處,亦不可棄之不顧。
清代醫家陸以湉《冷廬醫話》曾盛贊古方古法,但也有記載云:
“吳郡某醫,得許叔微《傷寒九十論》,奉為秘本。見其屢用麻黃湯。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,謂是足太陽表證,投以麻黃服之,汗出不止而殞。蓋南人少真傷寒,凡熱病無汗,以紫蘇、蔥白、豆豉、薄荷等治之足矣,豈可泥古法乎?”
可見,方不分今古,方不可泥古,有效為上。只是因為《傷寒雜病論》經方確實經典實效,故要更加重視罷了,但不可極左極右,轉為偏執。
后世如溫病學派所制之方,前人認為乃“羽翼《傷寒》”,因此在臨證之時,后世方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,以經方臨證者不可視而不見,否則將違背客觀事實,是對病家的不負責。
何況有不少后世方乃立足于臨證實際,從經方加減變化而來。一千多年來,歷代醫家都思考過《傷寒論》,根據實踐需求,對《傷寒論》經方進行了靈活加減發揮,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。前人研究經方的探索精神,值得今人學習。
再從《傷寒論》條文來看,張仲景在用方之時,也是靈活加減化裁的。列舉數條,如《傷寒論》
第14條:“太陽病,項背強幾幾,反汗出惡風者,桂枝加葛根湯主之。”
第20條:“太陽病,發汗,遂漏不止,其人惡風,小便難,四肢微急,難以屈伸者,桂枝加附子湯主之。”
第21條:“太陽病,下之后,脈促胸滿者,桂枝去芍藥湯主之。”第22條:“若微惡寒者,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。”
第28條:“服桂枝湯,或下之,仍頭項強痛,翕翕發熱,無汗,心下滿微痛,小便不利者,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主之。”
僅僅以上數條,便能看出張仲景對桂枝湯的靈活加減,臨證使用桂枝湯,根據實際情況不同,加葛根、加附子、去芍藥、去桂枝、加茯苓白術等等。
我們于臨證之時,應當效法張仲景“隨證治之”的精神,具體情況具體分析,根據實際情況加減用方。
以桂枝湯證為例。筆者臨證以來,也遇到過用桂枝湯不必加減藥味的情況。
如2001年,筆者在四川省德昌縣中醫醫院內科住院部工作,一日周末值班,忽來一賈姓患者就診,80多歲,為縣上退休老干部,本為內科主任的老病人,內科主任呼其為“賈叔叔”。
但那日恰逢周末,其他醫生休息,只有筆者值班,雖然筆者當時不過20出頭,患者為勉勵后學,也欣然求治于筆者。細問病情,原來患者近日感冒,癥狀主要是惡風、自汗出、頭痛、低熱。
筆者一聽,這是原原本本的桂枝湯證!當下處予桂枝湯:
桂枝15g,白芍15g,大棗15g,炙甘草6g,生姜7片(自加)。
其中生姜自加,不必開于處方中。大棗一味,患者告知其老家在山東,家中有山東大棗,遠比中藥房中的大棗好,要求也不開于處方中。
于是,處方中僅開桂枝、白芍、炙甘草三味,2劑,僅1.7元余,加上筆者掛號費1.2元,總共不到3元錢。
兩日后,筆者中午值班,甫至科室,正在穿白大褂,科室主任忽至,嚴肅問道:“你前天給賈叔叔開的什么方?”筆者心中一驚,以為前日開方有不妥之處,出了什么事,慌答道:“沒什么啊,就一桂枝湯。”
科室主任方徐徐道來:“賈叔叔說方子太好了,又便宜,兩劑藥才一塊多錢,吃下去就好了百分之八十。他今天再來找你開方鞏固,上午你不在,中午來找你。”筆者聽罷,心中一顆石頭方落地。
中午,患者果至,滿面春風而來,對筆者夸贊不已,言語之中,各種勉勵后輩之辭。再予桂枝湯1劑,痊愈。此后,老干部對筆者贊賞有加。時光荏苒,近20年,前輩勉勵后學之情,仍然激勵著我。
上述醫案便是為數不多可以使用桂枝湯原方不予加減藥味的例子。但是筆者臨床工作近20年,發現臨床使用桂枝湯,大多數時候需要加減,才更加準確。
桂枝湯一方,其味甘甜,臨床上若遇夾濕患者,使用原方不加減便不太合適了。
《傷寒論》第17條云:“若酒客病,不可與桂枝湯,得之則嘔,以酒客不喜甘故也。”便因喜酒者濕邪內蘊,桂枝湯味甘,服下則助長濕邪而嘔,故不可與。
臨床上遇桂枝湯證夾有濕邪者非常多,與當今患者喜食冷飲、水果等因素有關,也有外感風邪夾濕者,所以出現桂枝湯夾濕證。
這種情況下,筆者的經驗是,在桂枝湯的基礎上加厚樸、陳皮等,并視濕邪的輕重,若濕邪重,可再加藿香、白蔻、半夏、蘇葉、木香等,隨證選用。若桂枝湯證夾濕熱,可參小柴胡湯義,再加柴胡、黃芩等。
桂枝湯味甘而助濕,服過桂枝湯者都有此體會。一次,筆者給本校一名學生開方,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,學生反映服藥后雖然病情好轉,但是感覺藥太甜了,甜到“鉆心”,復診時訴藥味實在難以接受,要求調整。
原來,患者素體脾虛夾濕,故難以接受桂枝湯之甜,初診雖然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的基礎上已加用了厚樸、陳皮,尚不能抵擋桂枝湯之甜,于是二診再加木香、柴胡、黃芩,效果更佳,脾胃也易于接受。
2013年10月,筆者于昆明老區和呈貢新區兩處奔波,工作繁忙,教學加門診,日夜勞作,恰逢其時流感肆虐,終于病倒。
病初忽冷忽熱,1天后開始全身無力,惡寒發熱,惡寒時感冷到骨髓之中,四肢、腰背酸痛,并伴有輕微腹痛、腹瀉、腸鳴、惡心。腹瀉雖不重,一日一兩次,但腹瀉之前腹痛難忍。
因教學、門診繁忙,沒有時間抓藥熬藥,便先服中成藥與西藥治療,2天之內先后服風寒感冒顆粒、小柴胡顆粒、藿香正氣軟膠囊、諾氟沙星膠囊,無效。
2天后,家人擔心,勸說筆者去社區醫院治療,靜滴左氧氟沙星、克林霉素等退熱后又再次發熱。
退熱時出大汗,大汗后再發熱,發熱幾小時后再發冷幾小時,寒熱往來,然服小柴胡顆粒并無效,發熱時大汗不止。
10月12日,病情持續加重,怕風,四肢乏力,陣陣汗出,出汗濕透內衣,脘腹到臍周陣發疼痛,當日腹瀉一次,額頭蒸蒸發熱。
家人當日到重慶出差,家中只剩筆者一人。中午,實在痛苦難耐,忍著腹痛與發熱走到遠處一藥房抓中藥。
到藥房門口,筆者從包里找出一張空白處方,強忍痛苦,坐在街邊石凳上開方,歪歪扭扭寫下桂枝湯與桂枝人參湯(含理中湯)加減合方:
桂枝15g,白芍10g,大棗10g,炙甘草8g,生姜7片(自加),干姜15g,黨參12g,防風12g,蘇葉12g,厚樸15g,廣木香15g,炒白術12g。
1劑,水煎服。筆者抓藥后回家,忍痛煎藥。
服藥1碗后,不到1小時,額頭發熱便慢慢退下,自汗、腹痛、肌肉酸痛、無力等癥狀逐漸緩解,晚飯飲食終于恢復正常,服完1劑后,病即痊愈。
筆者亦素體脾虛夾濕,此次患病,為桂枝湯證,又兼有桂枝人參湯證,因脾陽虛夾濕,故在桂枝湯的基礎上,加理中湯、厚樸、廣木香、蘇葉等溫中化濕合胃,經方辨證加減,故覆杯而愈。
因此,經方完全可以根據患者病情進行加減,或者是經方之間相互組合,或者經方與時方組合,以達到最契合病因病機的狀態。
在德昌縣中醫醫院工作時,本院名老中醫何志業老先生尚在世,何老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便名列“西昌八大名醫”之中,與近代中醫眼科名家陳達夫先生等齊名。
坊間傳說何老先生年輕時曾拜縣中高人為師,得授《傷寒論》前半部真詮,即“太陽病篇”部分,即成一方名醫,可謂“半部《傷寒》治百病”。
何老先生善用桂枝湯,縣中百姓皆戲稱其為“何桂枝”,傳說用方皆桂枝湯。筆者在德昌工作時,何老先生已經90多歲高齡,仍然堅持門診。
一日,筆者在內科住院部上班,一患者拿來一方,請為轉抄,處方為何老先生門診所開,筆者邊轉方邊細看處方,見為杏蘇散也,于是笑著告訴辦公室中的同事說:“誰說何爺爺只會用《傷寒》方,只會開桂枝湯,這不是也開了一張溫病派的方子杏蘇散嗎?”
旁邊的副主任曾跟師何老先生1年,聞筆者之言,微微一笑道:“別看何爺爺開的是杏蘇散,實際也是從桂枝湯加減化裁而來,其實他并不了解杏蘇散這些溫病派的方子。他用桂枝湯時,比如見患者夾濕、夾熱、夾燥時,便會相應加減,一加減,桂枝湯便可變化為其他方。”
筆者聞言,頓時恍然大悟,何老先生運用《傷寒論》,乃取《傷寒論》之法,方是死的,而法是活的,他用桂枝湯,其實乃是用桂枝之法,若掌握了桂枝法,便可依據病情加減用方,一張桂枝湯便可千變萬化。
因此,從這一角度來看,后世時方完全可以視為經方的變方,前人說溫病派“羽翼《傷寒》”,是有道理的。再有,我們的前輩老師,在使用經方的時候,都會依據辨證法度,靈活加減化裁,我們后輩學者又何必要作繭自縛呢?
最后,筆者認為經方的加減化裁,可以有幾種情況:
第一,根據條文,依照《傷寒雜病論》原文加減;
第二,根據辨證,將《傷寒雜病論》中的眾多經方進行組合加減;
第三,根據辨證,選用《傷寒雜病論》常用藥物對經方進行加減;
第四,根據辨證,選用后世方與后世藥對《傷寒雜病論》經方進行加減。
筆者的臨證體會是,經方加減時,選用《傷寒雜病論》常用藥物對經方進行加減,比選用后世藥來加減療效更佳,因為這樣更加符合《傷寒雜病論》本身的體系。比如下面一案。
筆者母親,患腰椎病已10余年,10年前診為“腰椎間盤膨出”。2018年11月初,因氣溫突降,室外大風,連續幾日接送小孩上幼兒園,病情突作。
當日即腰痛,站立、行走、坐臥、轉側困難,緩緩而行、緩緩起身,不時牽扯,劇烈疼痛,有腰部無法支撐感,起床困難,睡臥于床。
第二天,筆者上班不在家,母親已自行服用布洛芬、對乙酰氨基酚等解熱鎮痛藥,又服中成藥壯腰健腎丸、金匱腎氣丸、跌打丸和中藥藥酒,又自做艾灸治療,均不緩解,不起于床。
傍晚,筆者回家,為母親診查,舌淡紫,苔薄白膩,脈弦緊,寸脈浮,辨證考慮風寒外襲,太少兩感。
處方擬麻黃細辛附子湯合葛根湯加減:
制附片15g(另包,先煎45分鐘),桂枝15g,生麻黃8g,北細辛6g,大棗15g,炙甘草6g,葛根30g,黨參12g,獨活15g,生白術20g,茯苓20g,生姜7片(自加)。
2劑,水煎服,一日半一劑。
當晚抓藥熬藥。母親服中藥1次,當晚安睡。翌日晨起,疼痛霍然減輕,已能自如起身、行走、下蹲,僅有輕微腰痛。
母親當晚服中藥覆杯而效,安然入睡時,筆者甚為欣喜,于是將醫案及處方分享到微信朋友圈,有學生留言問為何加用白術、茯苓。
原因是舌診見舌苔薄白而稍膩,考慮夾濕邪,加白術、茯苓利濕除濕。為何獨取此兩味?是取腎著湯之義,從腎著湯中取白術、茯苓兩味,是用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常用藥來加減彌補經方。
《蜀山醫案》是汪老師第一部個人醫案著作,可謂是字字從心坎出,將其幾十年中醫功底如數家珍地寫出,旨在“濟世活人”。中醫自古便有“惟愿世人不生病,哪怕藥架上灰塵”的宏愿,而這樣一本“良方起沉疴”的醫案輯錄,你值得擁有。
《蜀山醫案》的撰寫,從2016年跨越到2019年,2020年方得出版。本書為汪老師所著個人醫案集,系根據個人門診病案收集、整理、編按而成。掃描下方二維碼,識別可訂購。
《蜀山醫案》
官方正版
書中集錄了汪老師臨床治驗的疑難病證、危急重證及多年求治不愈的醫案,如四十五年咳嗽、二十年惡寒、七年糖尿病燥熱、七年咽痛、四年大小便失禁、三年自汗、一年低熱、三個月徹夜不眠、兩個月血尿、二十天高熱,以及IgA腎病、甲亢、蕁麻疹、銀屑病、硬皮病系統型硬化癥、肺癌晚期水腫腹水、類風濕關節炎、尿毒癥并心包積液、慢性阻塞性肺病、瘡瘍久不收口等中西醫皆為難治的疑難病或危重病醫案。是一部不可多得
(文章來源:金蘭中醫學社)



